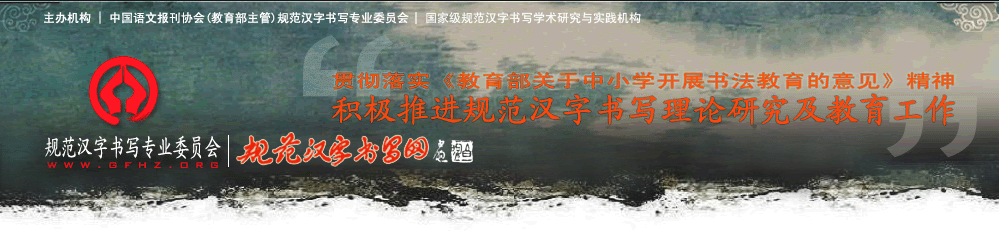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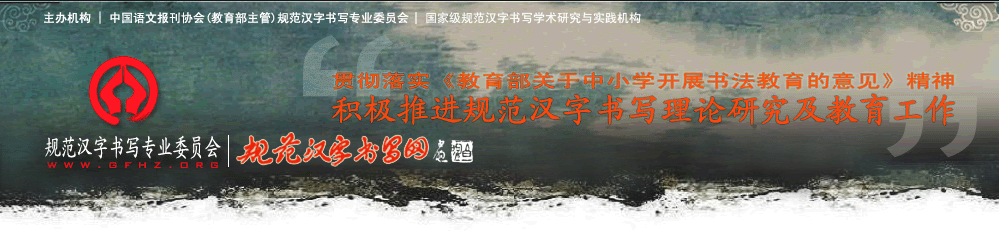
发布时间:2012-08-29 23:20:04 编辑:gfhz 浏览次数:
“文化身份”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它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前提条件。
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文化镜像中对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异性的某种认同。[1]一般而言,文化身份潜在地存在于国内外各种权力抗衡中,其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语言、圈层、社群等因素使得身份构成形成斑驳陆离的色彩,意味着个体存在价值与其文化身份不可须臾剥离,相反总是受到整体社会和族群的深刻影响。在后殖民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身份又与话语相关联。在赛义德的话语谱系中,身份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如全球化中的“身份存在”、权力话语中的“身份认同”、后殖民的“身份体系”等。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身份危机”、“身份冲突”“身份认同”、“身份建构”、“身份重建”等话题,[2]表明身份立场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大话题,同时说明全球化正在使人们逐渐失去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人们急于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共同体,以避免遭遇身份危机的虚无主义话语。[3]可以说,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
从另一个角度看,获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然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积极取向。文化身份不同与一般意义上的身份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个体的血缘家族辨识,而是群体、民族或国家人民和“他人”、“他群”、“他民族”、“他国人民”相区别,成为一个具有价值向心力文化共同体。在对自我身份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阐释的“双重焦虑”中,国人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同时,中国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大体上说,现代中国“确认身份”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打破旧文化、旧观念和旧体系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破旧形象”的时期。“五四”以降,中国学人一直在进行这种初级阶段的身份清理工作。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真正的自我历史、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的未来。丧失这种真正认识自我的前提,旧文化的魂随时都将重新附在新文化的肌体上。
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写时期,即去除旧秩序、旧形象的前现代性,而使自己在身份改写过程中确定真正的现代中国形象。现代中国形象,当然不是那种长辫、纳妾、束胸、裹脚、抽大烟等西方传教士刚进入中国时所津津乐道的形象,而是中国文化身份重新书写的新形象和新品格。如果今天仍以那种文化歧视眼光看待当代中国,将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现代中国形象已获得了自己的超越性价值立场、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和宽容的文化精神,这为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是新文化身份确认时期,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目的是揭露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力,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并重建自己已丧失的地位。[4]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但是在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却遭遇到诸多危机。这些危机的可以表述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精神遭遇到内在的撕裂:一方面,文化精神的承续,使中国文化仍然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衰亡后的唯一幸存者;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力中,中国文化被不断地边缘化。这种文化处境的尴尬,使中国文化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寻求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之路,并且使得文化论战成为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会诊。[5]
只有禀有了这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使自己既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属品,也不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认同者,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具有自己正当的文化身份。雅克•布罗斯说:“未来有赖于重要人物的正确决定。也就是说,有赖于中国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以及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如何看待中国。”如果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想象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输出将使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而非误读中国的前提条件。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富强,而且是生态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对话,从而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为重要的文化参照系。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人类生存模式,其生存质量有赖于彼此的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的程度。
就个体而言,往往是从文化集体无意识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记忆的。他在家庭、学校、社会中,逐渐形成自己具有民族烙印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方式、终极关怀方式,当其成长起来成为民族话语的担当者时,其民族身份则上升成为显意识而指导其行为。在民族文化共同体和参与社会物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具有中华性的文化意识。这样,无论他在全球化时代到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完全无法放弃自己的集体无意识和母语经验。就群体而言,文化身份包括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从事思想创新和文化批判的人,大抵能从思想表达中透出该民族对世界进程的看法,其中必然包含着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可以说,据此而形成的伦理观、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终极信仰等都成为其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丧失了这个核心层面,文化身份的辨识就出现困难。
古代中国人也曾经有过身份危机,大抵如元清两朝等,但没有像近代中国这样在面对西方强权时整体上对身份失落的危机感。读读晚清士人关于“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的争论,就不难看到这种在强国梦中潜在对抗西方的苦涩之心。而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前沿学者大都关注西方,并且在“追新而逐后”、“激进与保守”中去获得尽可能全面地“西方镜像”,这种对西方的研究性仰慕成为20世纪末西化风潮的基本症候,对中国当代文化身份的影响不可忽视。事实上,百年来国人深刻体认到:没有西方这个“他者”形象,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对话互动就是不可思议的。20世纪西学研究在中国占据独特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GDP在新世纪达到新的高度,关注东方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的东方话语入思角度受到新的重视。可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问题将不再成为世界的边缘性问题,而会受到国际话语更广泛更深刻地研究。那种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坚持全球化就是世界一体化的说法,将在中国现代经验中成为一种过时的另类性言说。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化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身份的烙印是特殊的。首先,个人的身份的组成是复杂的。有的可以有所蜕变,有的却终其一生,无有变化。比如出身,就不由得任何人选择,也永远无可改变。单就这一点,身份就永远各异。同是作家,但究其里,作家有出生城市的,有出生乡村的。他们的作品也烙下了他们身份的印迹,从作品里是可以品出他们骨子里的血的。因此,身份也就有所谓血统贵贱高低之分。这里所谈身份是就个体而言。
个体离不开国体,对国体中的个体身份而言,则是国家形象的代表,对祖宗血源的认同。改革开放之初的寻祖认宗,即为典型之例。每个国家的国民均为自己国家自豪,很少有否定自己所在何国的身份的。
我们从近代一路走来,对自己的身份的认识经历了不少反复与曲折,全盘西化者有之,中西结合有之……如今,走上了正轨。但是,依然有对西方过分推崇的。电影学院某研究生竟如此说:“我从此与诺贝尔奖无缘,仅仅因为一身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如果说,这句话是在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叶及中叶所言,情有可原,那个时候的中华民族正在探索崛起之路,局势动荡,很难有精力瘁心于科技,在国际中科技声名自然不振。同时,虽然文化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但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人脑海中都在想着富强二字,因此纷纷拿来,而淡忘了输出。欧美等西方国家,自然不可能全面认识中国,中国人出国受洋气肯定避免不了。据说,清末一显要出访欧美,此显要,似乎无咸菜无以就食,故随身携带了几坛咸菜。最后是,在他国海关过境时,咸菜成为他们过境的障碍,咸菜被彻底化验了,方被放行。小小咸菜,惹出如此麻烦!当然,咸菜本身是无辜的,虽然欧美通过化验看到了咸菜的功能,但欧美人心里依然以怪异视之。这些零碎一组合,在他们眼中,中国就是希奇古怪的集合体。甚至到今天,中国电影输出由“三寸金莲”之类转换成大风歌,这对中国民族文化输出未尝不是一个转化,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一件好事,但欧美却有些诧异不解,一时难以回过神。可见,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输出亦是有误区的。欧美一向不能正确认识中国,中国自己应该负一定责任。不过,真正的能人,欧美是不排斥的。所以,过去的年代,因种族皮肤之异,未有得到认可,是有可能的。但如真是上乘的英杰,他国亦是敬重的。
那么,是否是我们自己的文字的问题呢?西方难以谙熟中国文字,中文翻译成英文又不地道,这阻碍了理解识读,遂使西方不能真正全面了解我们,使我们与诺贝尔奖无缘。其实,这也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如今,我国的教育,大部分时间是花在英语上。本科生的学位需要英语来证明,硕士博士入学需要英语来证明,我们都快变成英语的国度了。诺贝尔文学奖有我们吗?法国从来以自己语言为骄傲,他们可不会天天学英语,诺贝尔奖与他们绝缘了吗?
肤色、语言均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已经遗忘了身份!
我国自来崇尚礼仪,友待邻邦。因为,我们曾经是天朝大国,四方均为夷狄,后来,即使这个四方概念变了,遥远得我们都不知道在何方,我们仍然泱泱大国之风不变,最后是竭地力以搏他国之欢。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终于开启了国门,虽然亦有了经验教训,知道拿来,却没好好宣传自己,泱泱大国似乎只需要别人来认识我们。因此,长期以来,我们的国际形象是片面的。而当我们大国的自豪与自信被打击后,国人的心理开始变化,全盘西化亦有了一定市场。西化发展到极致,则是投入他国怀抱,真正地完全崇洋媚外。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再加以我国建国后,曾有一段经济低靡、精神困惑期。当改革开放一来,于是西方什么都是好的。我们其中一部分人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虽然,我们有识之士一再呼吁振奋民族精神,宏扬传统文化,但这个症结或多或少烙入了国人心中。就连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亦非得去国外镀镀金,似乎没有洋气,就成不了气候,无论学中还是学西的。思来,不无怅然!
我们没有必要从西方人的眼神中寻觅自己身处何方,中国人最可悲处在于盲目遗忘:遗忘责任、遗忘历史、甚至遗忘自身的成就。既然我们有能力创造与传承强势文明,我们何必在西方人面前如此萎缩、苟且?学中国学亦么必要非到西方一遭,才能最终显名国中!
中国有一个词叫“洋气”,大约就是说无论东洋,还是西洋,只要能有幸沾沾,就“气”十足了。这个“气”到底是什么?是内在修为,表现于外在的气质,还是什么?一直没搞懂。但更纳闷的是中国本早就讲“气”,从孔孟一直到张程朱王,从儒家到释道二家,但似乎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去领会。为什么洋之气就这么容易深入人心,要得全民为之膜拜而倾倒呢?!
更甚的是,现在还有些学者拥抱、迷恋大众文化,至而扬言中华民族西化不够,还需殖民百年,直至全盘西化方才罢休。此等言语出自中国知识分子之口,实在令人瞠目。当部分西方人逐渐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而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竟堂而皇之地作践本国文化。中国人是不是过分着迷于西方利益与金钱的现代化?是不是已经放弃了民族文化的捍卫意识?
在大国崛起之时,我们不要忘了警惕身份遗忘!
--------------------------------------------------------------------------------
[1] 参王岳川《中国镜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 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参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大学2002年版;梁展遍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2002年版。
[4] 参(美)斯维德勒著《全球对话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刘梦溪《百年中国 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中认为:“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皅利”打开的。……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